【编者按】:“我一个农村孩子,怎么就成了西北政法的学生?”——1991级校友王学堂在《青春都在西北政法》中写下的这句深情叩问,如投石入湖,瞬间在万千西法大人的心间漾起层层涟漪。
这篇文字不仅牵起无数校友关于高考的青涩记忆与择校的绵长情缘,更掀起了一场跨届别的温情“回忆接龙”。校友们纷纷提笔,循着这份意趣,以各自独特的视角,畅叙当年与西法大结下的奇妙缘分。一篇篇饱含深情的回忆文字,像春笋破土般次第生长,蓬勃涌现。
从本期开始,我们将陆续推送这些镌刻着青春印记的故事,邀您一同回望那段闪闪发光的流金岁月。
同时,也诚挚邀请广大校友提笔书写,分享您独一份的记忆,让我们一起编织属于全体西法大人的永恒记忆画卷。

壹
我是1991年参加高考的。这之前,村里已经出七个大学生(含专科,那时叫大专院校)。对于一个只有三十来户人家的村子,这个比例似乎不低了。但我的家乡是素有西北高考“状元县”的会宁。我的同学兼邻居田圃(吉大教授,留美博士)兄妹四人都考上了大学。我们的化学老师王彦强更是一门三博士。那时候我是化学课代表,我记得王彦强老师站在讲台上自豪地说:我哥哥在芝加哥大学留学,是中国第一个环境学博士。那一年他的弟弟王彦灼考上了北航,后来也去美国留学。王老师当了几年高中老师,兜兜转转几年后也去了美国。前几天刷到一个小视频,王老师所在的会宁新塬乡出了71位博士,镇上还立有一块“博士墙”,上面详细刻着每一位乡里出的博士及毕业院校。

我的小学是在村里的田家坪小学上的,那是一个地主家的院子改建的。现在想来,那个院子很不错,墙很高很厚。我们在他家的瓦房里上课,屋檐下还有燕子垒的旧窝。后来因为孩子多,需要扩建,前院的墙被挖倒盖了两间大教室。据说学校旁边一户人家挖出了一坛子的银元,地主家的后代(住我家门前)还去讨要。那时候一个银元可以兑换10元人民币。我经常在心里琢磨,一坛子银元能换多少钱呢?不得……我想不出那个数字有多大,那可是上世纪70年代末!
从我家到学校大概有半里路,要从“畔”(高而陡的坡)上走下去。我经常和伙伴们徘徊在“畔”上的沟沟坎坎掏鸟抓虫,直到听见老师敲响上课的那块铁铧犁时,才风一般冲向学校。因为没人照顾,父母早早把我打发去了学校。我的一二年级读了四五年,不知学习为何物,遇到天冷就不去。但夏天的中午会早早去学校,为的是能在学校后面的祖历河泡水。那时候的河水很清,一头潜下去能看见河底的石头。有一天,我父亲罕见地来了趟学校,他走访了每一位代课老师(其实就是几个略微识字的农民),得出一个结论:这个娃如果认真的话是块读书的料。于是,父亲托人将我转到了镇上的中心小学。现在看,父亲的这个举动改变了我的人生。我不知道他出于什么样的动机,从时间上看那时候恢复高考了。
镇上距我家有五里路,为了上学不迟到,必须早早起床。我妈妈要起得更早为我做饭,她能够凭着鸡叫声准确判断出时间。但有时候也错,我们经常起早,吃完饭天还一片黑。妈妈说要是有个闹钟就好了。我记得镇上商店里有卖的,三元钱,但我们舍不得买,农村人会把钱留着用在最紧要的地方。我总是第一个到校,从家里出发的时候常常有星星月亮相伴。有时候到校门口,大门还没开。在转学一个月后,我堂哥(后来早我一年考到当时的西安纺织学院)也转到了镇上小学。他们家有闹钟,不会错过时间。他出门的时候会唱一首歌,每当他那“左嗓门”歌声响起我就出门,我们在路口会合,结伴去学校。
镇上的小学校舍整齐,我转学的那年刚刚翻建,红瓦白墙,玻璃窗宽大明亮。一个班级有五十个学生,老师是正规的师范毕业生。坐在那样的课堂上,人自然迸发出学习的热情。我开始认真听讲,争取把每一篇课文背下来。几次考试下来 ,我的成绩都在前几名。这极大地提升了我的自信心,原来我也行。自此,我的学习动机变得极其简单:考第一。回看我的求学之路,都是跟这一目的较劲。至于上大学,通过学习改变命运,那是非常遥远的事。一年后,原来的五年制小学改六年制,我因为成绩好被调到六年级。小升初我考了全镇第二名,那天傍晚我赶着几只羊回家,在村口碰到几个大人,他们说,“你考了第二,街上贴着大红榜!”第一名是学校对面木器厂厂长的儿子,是位复读生。
这是我人生中第一次体会到成功的喜悦。我很想亲自去镇上看看,看看自己姓名被写在红榜上的样子。但我实在没有时间,我得照看家里的五只羊,每天得把它们赶到山上去,顺便得为家里的毛驴搂一背篓草。作为农村孩子,总有干不完的农活,从暑假开始,先扁豆熟了,接着是豌豆,麦子,小孩和大人一样忙活在地里,收、晒、碾,直到送入仓,有时候晚上睡在谷场上。为了增加经济收入,我们家还会种些西瓜蔬菜卖。四年级的那个暑假,我每天要拉着一板车西瓜(20个左右)去两个村以外的化工厂门口去卖。那段时间,我的台球技术进步很快。工人们常常和我赌球,如果我赢了,他们就买我一个西瓜。我不喜欢干农活,机械重复的动作常常让人麻木。但又将此当做必然。当然,也有快乐的时候,比如放驴、羊这种差事,细雨蒙蒙中,和小伙伴把牲畜赶到山上,在放羊人挖的山洞里打一会儿扑克,或是到后山的邻村去偷一窝土豆烧上。如今回想起来,那成了我人生最美好的记忆之一。
贰
上初中后,家里的条件好了,我可以骑着自行车去学校。在初中,遇见了对我一生中影响最大的田绿洲老师。他鼓励我们写东西,办黑板报、手抄报。这些东西不同于课堂作文,可以自由表达。他还把很多的私人藏书借给我们看,这对于农村孩子来说是真正的“精神食粮”。有天放学路上,一辆货车翻了,车上的水果蔬菜洒落一地,过路村民热情帮助。我把这件事写下来送到镇上的广播站,播出后得了1.2元的稿费。这件事极大刺激了我的写作热情。说到写作,不得不提一下我的同学田发春。有一天他拿来一本“神秘”的书让我看,原来是一本抄在牛皮纸上的剧本,像是《秦香莲》。那些被反复翻阅过的牛皮纸暗黑光滑,上面的文字朗朗上口。那是我第一次读这种“另类”文字,有种奇妙的感觉。我觉得那种带着韵律文字才是最美的。发春的父亲叫“四十”,是个秦腔迷,生、旦、净、丑样样会。他生了七个儿子,人生艰难而不失乐观,常常赶着一群羊在山坡上怒吼秦腔。我开始着迷秦腔,为那样的文字与内容。初三那年干脆“跟社火”,穿长袍挂胡子,走村串巷。有时候从别的村回来天大亮了。我还迷上了二胡、唢呐。从我本家的哥哥家借来二胡,坐在午后的树荫下,咿咿呀呀地拉。我的中考成绩不理想,没有考上全县的重点高中,又复读了一年。我不知道那是否与玩这些有关。
高中我读的是大名鼎鼎的会宁二中,这个学校的学生基本都能上大学。第一次远离家乡,我发现同学们竞争性非常强,那种靠“聪明”的学习不行了,必须下功夫。同时,我们必须自己动手做饭。一般是用一个煤油炉,切几块土豆,煮些面条,要是能打个鸡蛋,那简直奢侈得不行不行。我和同学会每两周轮流回次家,骑车走过四十里公路,从家中置办些面粉、肉臊子、土豆等吃的。最让人难受的是晚上四十个人挤一间大宿舍,味道太难闻,根本无法休息。我和武同学、高同学一商量,干脆抱被子去教室睡。几张课桌一拼就是一张床。我们在教室里睡了一年,直到高二分科有了新宿舍才搬回去。在教室“露宿”的日子让人难忘,去年休假我特意去找几十年未见的武同学,为的是一起怀念下当年住教室的时光。我记得他会用自制的“锯条”加热器,在教室的插座上烧开水。我们躺在坚硬的课桌上畅想人生和未来。有天早晨醒来,窗户一片白,原来下雪了。
我高中的时候对历史起了兴趣,读了不少故事书,还写了一篇如何学好历史(有关记年方法)的作文,被老师拿去推广,还得过全校的文史知识竞赛第一名。分科的时候被班主任点名要了去。他对我的期望很高,希望我考一个名牌大学好让他“光耀门庭”,遗憾的是我天赋有限,无法达到他的要求。他认为我不认真,太贪玩,常常在下晚自习后的宿舍门口逮我,把我往教室赶。我感觉在三个小时的高强度学习后,再也没有一丝力气了,得赶紧回宿舍睡觉。我在高中时迷上了踢球,打乒乓球。高三时班上插进来了二十多名复读生。我们被调到一个大会议室上课,往往下课铃还没响,就从窗户翻出去占球台。我们八班(文科班)的学风全年级最差,是校长、副校长“关注”的重点。有天晚自习,我正和后座的宋同学说话,冷不丁脖子被人抽了一巴掌,火辣辣地疼,抬头看一人怒目圆睁,原来是王副校长!
高考的那一两个月,我完全不在状态。天气热(那时高考在七月)加上压力大,整日脑袋晕乎乎的,根本没心思学习。每天只是象征性地看看书。大部分同学和我一样,我们只是在等待,等待那个决定命运的日子到来。高考的那一天,我同桌兼同床何同学(当年被录取到东北师大)整晚睡不着。我则和往常一样倒头大睡,太累了。开考前不知道谁透露的消息,同学们跑到校门口的黑诊所打针——注射葡萄糖,说那玩意能增强“持久战”能力。于是我也花了七毛钱打了一针。但我的每门课都是提前交卷,历史、地理都是不到一小时出了考场,感觉考题都见过,大同小异,如今看草率了。
三天的煎熬终于过去,作为农村孩子,我又投入到繁忙的农活之中。我的志愿是委托班主任老师填报的,对学什么专业,我持开放态度,农村娃能考上个大学,摆脱一辈子与土地打交道的命运就不错了。放榜的日子,我父亲首先坐不住了。有一天,他给我两块钱,让我去县城看看。我搭班车去学校,头上还戴着干活的草帽。在教务处的大黑板上,陆续写着已经被录取的同学姓名,但没有我的。那时候我已经知道我的成绩超过了本科线,怎么会没有呢?我变得焦急起来,快到中午时,邮递员来了。那时的录取通知书是用挂号信寄。他把一大包的信件送进收发室,立即有一群学生围上去。负责登记的许校长夫人把我们往外赶,说她统计完后会写在黑板上!我爬上窗台挤着脑袋看,正巧看见了我的名字,底下是红色的舒体“西北政法学院”。我激动地从窗台一跃而下,一颗悬着的心终于落地。自此,我成为了西北政法的一员。四年的学习一晃而过,因为怀揣一个当兵的梦,毕业后我去了部队。从21个人的兵头排长干起,直到团级退役。2006年,我重拾专业,当起了律师。业余写了几部有关律师的文学作品,今年是我们毕业三十周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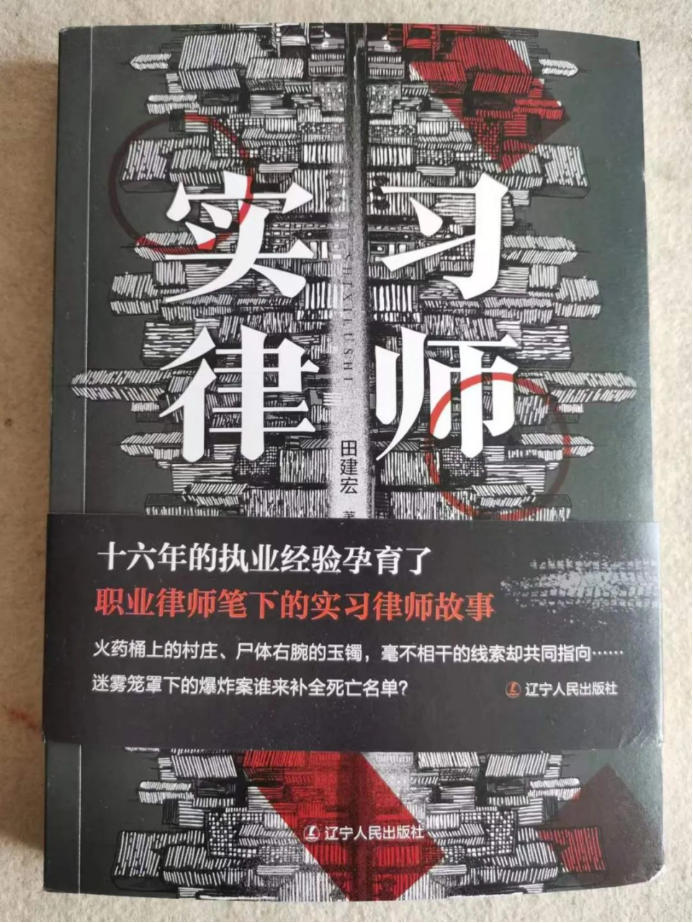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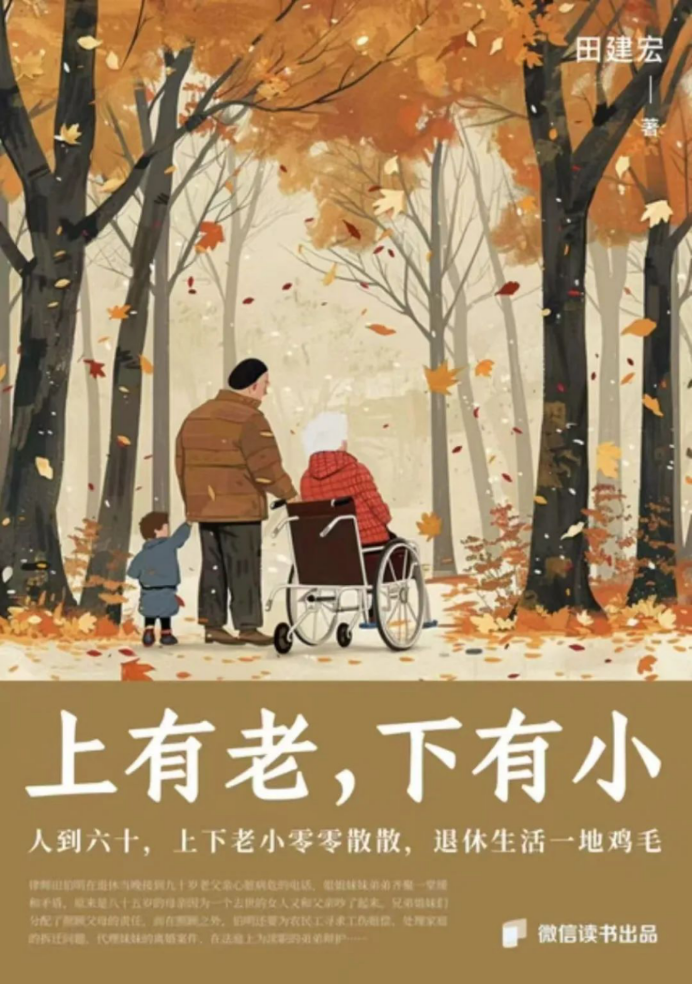
叁
我常常想,假设那年父亲没有把我转到镇上的小学,假设我没有上大学,人生的轨迹将如何?
我的故乡以“苦甲天下”闻名,至今还很贫穷,但几乎每个农家都有大学生。那年我们班录取了13个人,全校上本科线的有240多人。其他同学在复读两三年后基本都考走了。我常常想,是什么促使这个贫穷的地方如此重视教育?一方面是通过考试摆脱底层命运的强烈愿望,一方面是仰仗重视教育的传统。最近我读两晋南北朝史,在中华民族最为动乱黑暗的三百年间,无论漠视文化的北方蛮族还是倡导清谈嗑药的两晋都没完成民族的统一,反而是张轨及其后人在陇西一带建立的凉(包括前凉、后凉、南凉),重拾两汉时期的儒学,强调“担当与秩序”,大兴教育。以李冲(甘肃陇西人)为代表的这批人(约三万)后来在北魏大展拳脚,促进汉化改革,“关陇集团”的兴起,奠定了后世的隋唐盛世。我的故乡虽然贫穷,但一直有重视教育的传统。
人们喜欢把高考称为“鲤鱼跳龙门”,暗示阶层的跃迁,第一名也叫“状元”。实际上,如今的高考与先前的科举有本质的不同。中国从汉武帝时开始设国学,教授儒学,第一期五十人,王莽时期达到三千人。学满几年后,优秀的可以选拔当官。也有征辟、举孝廉,孝顺父母可以当官。千万别小看这个举孝廉,二十万人口的州才能推荐一人,不满这个数的二至三年推荐一人。两晋南北朝时期实行“九品中正制”,只有门阀子弟才能当官,寒门子弟基本无望,只到隋唐科举取仕。此后一直到民国时期,废除科举,西学兴起,教育平权时代来临。
父母去世后,我很少回故乡。端午时我给家族年纪最长的叔叔打了个电话,年近八十的他在给花椒树打药,我说你该歇歇了。他说闲不住,农民的命啊!我安慰他说,现在多好,不用交皇粮(土地税)了。据我所知,历史上只有汉景帝时有十多年不纳粮。他悠悠地说,好是好,可村里没人了,只有他们一些上岁数的老人。他的话让我瞬间泪目。当年想尽一切逃离的山村,我们的根还在那。我怀念小时候脚步走过的每一个沟沟坎坎,怀念一个人走过空旷山谷的寂寞,我怀念草绳勒在肩膀的那种疼痛,我怀念……我去过全世界十多个国家,唯有那个山村让我如此魂牵梦萦。如今,我也在奔六的路上,我不知道将来魂归向何处。如果有可能,我希望被埋葬在故乡,就在父母的坟旁。
行文至此,突然收到孩子发来的一张上课截图,周围是几个头发花白的同学。他的同学大多是工作一、二十后,又回去读大学的。去年,他收到一所顶级大学的通知,又主动放弃到一所普通的大学跨学科读计算机,为的是好就业。当年,我们毕业就能找到工作,最差也是县级公检法,而他们却在为工作发愁。教育再也不是改变身份地位的途径。教育是人的一项基本权利,不因阶层的差异而不同,她像生命权一样不可剥夺。教育不但决定个人的命运,也决定一个民族和国家的未来。

本文作者田建宏,男,甘肃会宁人。1995年毕业于原西北政法学院,曾在第二炮兵某部服役十年,退役后从事律师工作。业余著有《小律师办案记》《实习律师》《上有老下有小》及短篇集《辩护律师手记》等作品。现为山东正洋律师事务所律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