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我一个农村孩子,怎么就成了西北政法的学生?”——1991级校友王学堂在《青春都在西北政法》中写下的这句深情叩问,如投石入湖,瞬间在万千西法大人的心间漾起层层涟漪。
这篇文字不仅牵起无数校友关于高考的青涩记忆与择校的绵长情缘,更掀起了一场跨届别的温情“回忆接龙”。校友们纷纷提笔,循着这份意趣,以各自独特的视角,畅叙当年与西法大结下的奇妙缘分。一篇篇饱含深情的回忆文字,像春笋破土般次第生长,蓬勃涌现。
从本期开始,我们将陆续推送这些镌刻着青春印记的故事,邀您一同回望那段闪闪发光的流金岁月。
同时,也诚挚邀请广大校友提笔书写,分享您独一份的记忆,让我们一起编织属于全体西法大人的永恒记忆画卷。
前一阵校友王学堂发了一篇《我一个农村孩子,怎么就成了西北(政法)的学生?》,王敏琴写了《我一个江南姑娘,怎么就成了西北(政法)的学生?》,苏晓凌续了《我一个赵国人,怎么就去秦国(西北政法)上学了?》…… 这一发不可收拾,便热闹起来了,大家纷纷动笔,按照保持队形不变的原则,我就起了这么一个哗众取宠的题目,向各位看官汇报我一个秦人固守长安选择西北政法的心路历程。
我出生在西安郊区灞桥长安蓝田交界的乡村,作为土生土长的秦人,我三次参加高考,第一志愿都是西北政法,固守长安,不愿出秦周游列国,陕西人固执倔犟的性情可见一斑。说起原因,就是陕西人乡土情结浓厚,故土难移不愿出远门,嫁姑娘都不对外,选择学校也是如此,陕西高校排名全国前三,而且985、211院校众多,本地学生选择余地大,而且对于政法专业来说,西北政法位列五院四系,论学术氛围比综合大学更专更强。总之一句话:西北政法性价比高,这是大实话。
其实,我从小喜欢文学,初中高中时就不务正业创办文学社,还聘请著名作家陈忠实当我们的辅导员,可以说,我小时候的梦想就是长大当作家。
与西北政法结缘,源于高中时的一次演讲。那是高三的时候,初夏时节六月初,在纺织城五厂坡上面的高台上,一个自称是西北政法的学生,高高的个子气宇轩昂,挥舞的双臂激情澎湃,他大声疾呼般宣讲着民主法治自由,讲得是那么动情讲得痛哭流涕,在台下观众里翘首倾听的我,虽是初夏的灼热天气,却感动得起了一身鸡皮疙瘩。
那一刻起,我心中的文学梦,就变成了法治梦。当年的高考,第一志愿我毅然而然报了西北政法,秦人不离长安。然而天不遂人愿,我的分数只能上大专,我给父母说我要补习,继续考西北政法,秦人不弃长安!
谁料想,第二年高考前夕,我淋雨后感冒发烧,吃了退烧药害怕考场上迷糊,妈妈又找医生给我打提神的肌肉针。昏昏沉沉下了考场,我知道今年离西北政法分数线更远了,但第一志愿仍然是报了西北政法,秦人固守长安!
考试成绩出来了,不如前一年,但能上中专。爸爸说:“农村娃,能上个学,跳出农门,已经不错了,谁还把你往老供给呀!”
我心里千万个不愿意,泪流满面地捶着墙,妈妈默默地哭了,好强的她,这些年辛辛苦苦贩鸡蛋卖米面,也是希望儿子出人头地啊!好在我们家里是妈妈做主,她坚定地说:“娃呀,只要你愿意努力,我再苦再累都供给你!”
有了妈妈这句话,我又找人修改志愿(中专录取了就不能再参加高考),再次踏上了令我刻骨铭心愁肠百结至今仍梦中惊醒的复读之路。
煎熬痛苦的复读过程,这里就不多说了,回忆无疑是再次揭开累累的伤疤。第三年高考出榜,高出一本线近二十分,我终于上了线,第一志愿仍然是西北政法!我的学号是910009,意味着我是第九个录取的。妈妈高兴坏了,爸爸也露出了笑脸,摆流水席大宴亲友乡邻,我内心的喜悦自不言表:终于如愿以偿考上了梦寐以求的西北政法,秦人固守长安,得胜!
经历了三年炼狱般煎熬的高考,大学生活可以说是丰富多彩,除了正常的专业课之外,我下海当倒爷,贩卖衣服鞋袜,包电影放录相,当然不忘秀一笔所谓的好文笔。在院报发表了几篇小作文,正好被宣传部负责学生通讯社工作的高霄老师看到了,他让人通知我到他办公室,问我愿不愿意参加学生通讯社。学通社可是西北政法第一学生社团啊,我不假思索地就答应了。从此,真正踏上了热爱文学的道路,也和高霄先生成了几十年亦师亦友的好朋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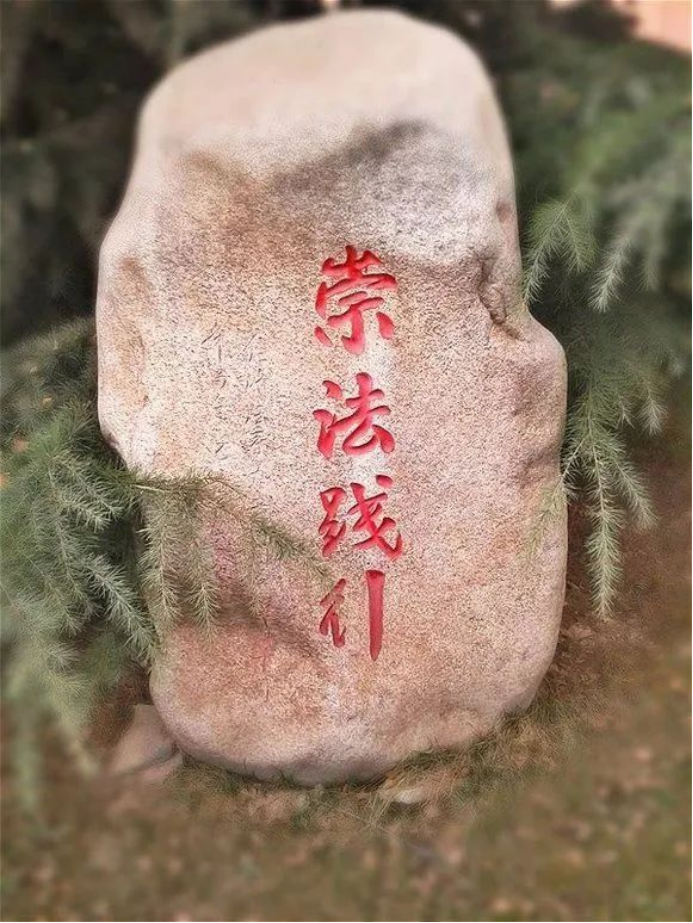
大学四年青葱岁月的校园生活,这里就不一一赘述了,我曾经写过一篇《昨夜星辰昨夜风》的回忆文章,有兴趣的可以寻来一读。
大学毕业,那时候大学包分配,政法学生还是很受欢迎的,我们班42个学生,主要分三大块,北京深圳西安各有七八个,其他同学基本都回原籍了。
九零年代初,交通不发达,网络刚起步,毕业时大家都想着,西安一别,恐怕是天各一方,以后很难再见到面了。于是就出现了很多难舍难分的场面。在火车站,男女同学依依惜别抱头痛哭,有的情侣甚至恨不得冲到铁轨下面去,行政法的一个老师与学生感情特别深厚,他不忍心和同学告别,而是一个人跑到校外的野地里,躲得远远的,他怕控制不住痛哭难过。
那半个月的离别场景,同学录上写留言,互赠纪念品,安徽的陈儒抱着吉它唱《山楂树》,他唱得泣不成声,手持录音机的我泪流满面。
最后离开学校的我和小广东林建鹏,在空旷的校园里转悠来转悠去,一遍遍听着录音机里小虎队的《祝你一路顺风》:
那一天
知道你要走
我们一句话也没有说
当午夜的钟声 敲痛离别的心门
却打不开我深深的沉默
那一天送你送到最后
我们一句话也没有留
当拥挤的月台挤痛送别的人们
却挤不掉我深深的离愁
我知道你有千言你有万语却不肯说出口
你知道我好担心我好难过却不敢说出口
当你背上行囊卸下那份荣耀
我只能让眼泪留在心底
面带着微微笑用力的挥挥手
祝你一路顺风…
祝你一路顺风
写到这里,请原谅我又一次落泪了。离别的许多场景,至今历历在目,四年政法缘,一生政法情,且行且珍惜。
有一个特殊的场景,已经时过境迁了,也写一下吧!毕业前夕,因为某些原因,大家情绪爆发了,在宿舍里撕书本向楼下扔,甚至有人喝了酒往砸暖水瓶,场面逐渐有些失控,宿舍楼道也写满了许多乱七八糟的东西,记得最清楚的一句话是:政法给了我黑色眼睛,却让我寻找光明。学校领导震怒了,开会大发雷霆,我们系二班的一个四川同学,自告奋勇站出来解脱了大家,很男人挺有担当的。
不谦虚的说,因为社团干部学生党员文笔好,我当时还是挺吃香的,北京的《法制日报》,深圳的法院等好几个单位想要,但最终还是选择了留在西安,因为老祖母已经80多岁了,她不愿意我离开西安。当初选择西北政法,毕业留在西安,原因说到底,还是陕西人乡土情结太深,觉得哪里都没有家乡好,老婆孩子热炕头,没有闯劲不愿离开老家。
毕业实习在西安中院,本意留在中院,却不想市纪委招人,幸运地进了市委大院,这是我走上社会的第一个工作单位,教会了我很多的东西。在纪委工作十年后下基层,也扎根在了泥土里,宣传部街道办文化局,二十年走了十几个单位,可谓经历丰富但经验尚欠缺(我一个老同事形容我是跛子穿裙子--扭得欢走得慢,职级十几年原地踏步),虽然无甚长进,倒也丰富多彩,人生如此,不亦乐乎?风风雨雨,兜兜转转,前几年又到了司法局,终于把老师教的学问派上了用场,为法治建设添砖加瓦贡献余热,干得风风火火,自我感觉良好,人生这般,不亦乐乎?

曾经填过一首词《满江红》:
早春三月,已然是,百花烂漫。
抬眼望,千里长安,雾隐南山。
四十八载功与名,纪委文化和街办。且从容,忆少年白衫,菩萨蛮。
喜路遥,爱金庸,文字痴,侠义胆。持长剑,茶酒诗书相伴。
壮志凌云信天游,逛吃行吟江湖间,待从头,重走锦业路,乌衣还。
还写过一首诗《随感》:
左手执剑右捉笔,任侠之风书生气。
仰天长啸傲云霄,席地低吟水流西。
青丝千缕惜春去,白发万丈唱黄鸡。
无聊常忧世间事,有钱难买我愿意。
这两首诗词是我喜欢的,高度概括了我这些年的工作生活和处世态度,感谢西北政法塑造了我的人格,正如校训所说的“严谨求实文明公正”,有如此信念加持,使我行走如沐春风,所向皆为阳光坦途。
五十五岁回望人生路,打油诗一首结尾:
秦人固守在长安,西北政法一生情。
岁月沧桑再回首,昨夜星辰昨夜风。
学海无涯少年志,社会有责白头翁。
公平正义担在肩,不忘初心勇前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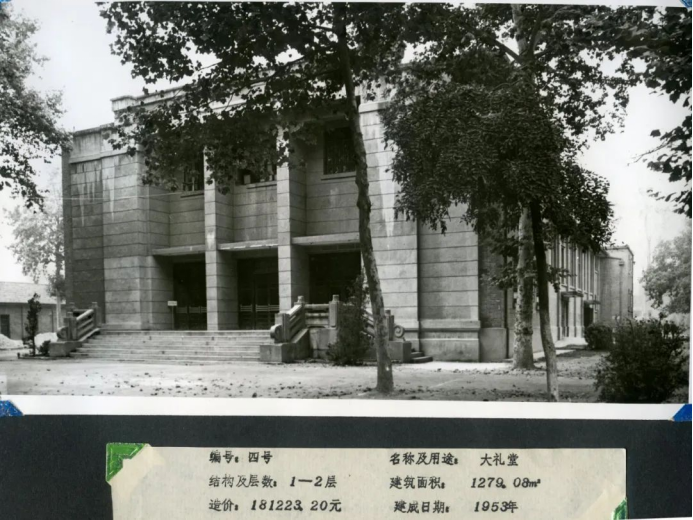
本文作者周琦,西北政法法学系1991级校友,现在碑林区政府部门任职。著有长篇小说《乾坤湾纪事》、《雉鸡翎》以及中篇小说《血很热,手很凉》、《鲸鱼沟》等百余万字。